5月18日,“千年酒韵 大国兼香”濉溪酿酒遗址展示馆开馆暨酒文化交流研讨会在淮北举办。
圆桌对话环节,山西大学考古学院院长、教授高大伦,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智彬,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、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陈剑,安徽省文旅厅考古处处长潘海涛以及口子酒业党委书记、常务副总经理徐钦祥一起,围绕濉溪酿酒遗址的价值独特性进行了深入探讨。

|山西大学考古学院院长、教授高大伦
此外,高大伦还表示,濉溪酿酒遗址是遗址发现之后建成展示馆最快的,可见当地政府和酒企对酒文化的重视。

|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智彬
第二阶段从90年代末到2015年左右,该阶段把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运用到酿酒遗址的发掘研究当中,主要遵循二元证据,即考古发掘的结果和古代文献相互对照、相互对应,当时的科技检测是浅尝辄止。
第三阶段从2015年左右至今,体现为酿酒遗址考古发掘的规范化,对酿酒遗址认定的标准化,还有科技检测的全面化和系统化,当前就属于这一阶段,酿酒遗址考古的理论和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。
孙智彬表示,濉溪酿酒遗址在第三阶段具有代表性和领先性。

|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、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陈剑
陈剑则表示,借着濉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开馆的机会来到濉溪,让他想起了三个联系:
首先,1999年,水井坊考古遗址发掘,并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,同年入选的还有淮北濉溪的柳孜运河遗址;2001年,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水井坊遗址与柳孜运河遗址同时入选;目前,水井坊遗址和濉溪酿酒遗址,都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。
他说,“这是我与淮北濉溪、与口子窖的多年‘神交’,也是川酒与徽酒的联结。”
在他看来,无论从规模还是工艺流程的完备性而言,濉溪酿酒遗址都是中国酿酒遗址的杰出代表,其属于中国传统工业遗产的范畴,但又具备文化属性,且直接关联大运河世界遗产。
目前口子窖传统酿酒技艺,已被列入安徽省非遗,陈剑也期望它能尽快列入国家非遗。

|安徽省文旅厅考古处处长潘海涛
他还表示,此次濉溪酿酒遗址展示馆的开馆,多方合作,多方联动,一方面可以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,一方面又可以推动企业文化更久远、更有高度。

|口子酒业党委书记、常务副总经理徐钦祥
“一千年前,这里的古人就埋下了根。坚守匠心、传承创新,让口子窖兼香在新时代焕发更璀璨的光芒。”徐钦祥说道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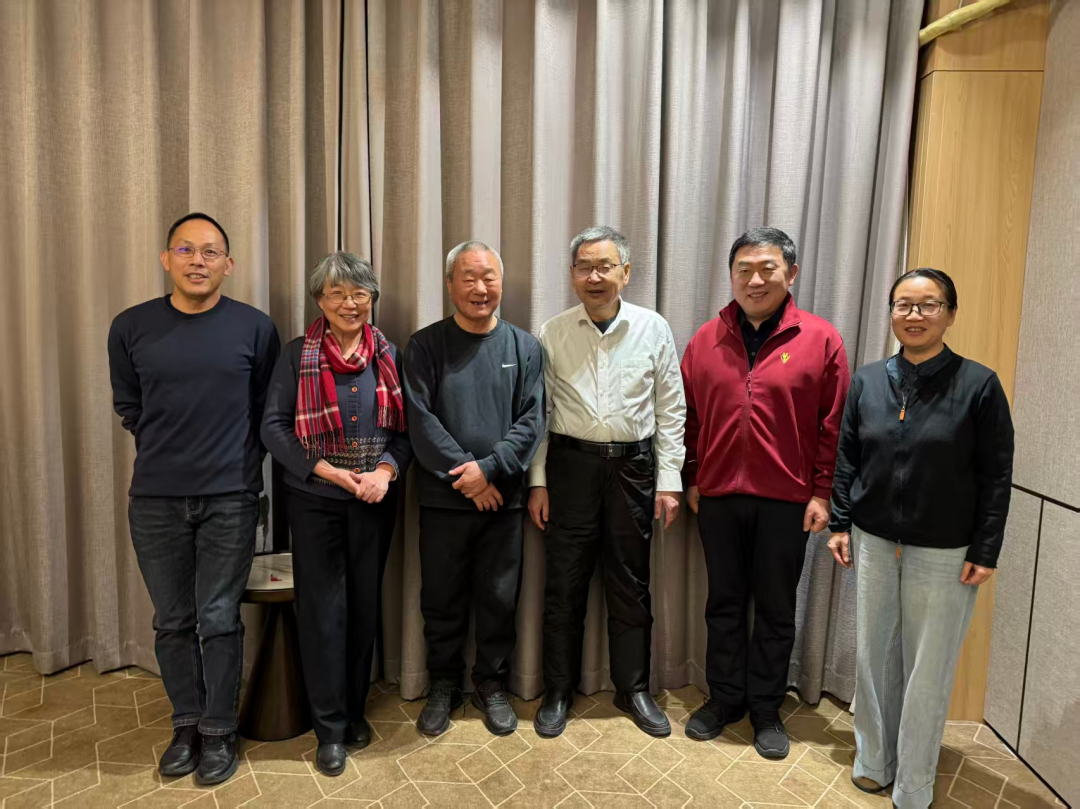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